今年清明,去拜祭中國初代美食KO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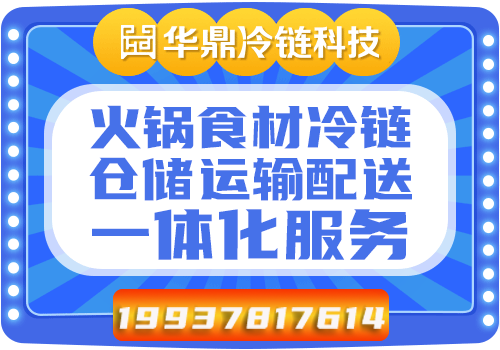
編者按:Christopher St. Cavish曾是一名西餐廚師,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中餐愛好者。他會帶著量尺與秤,完成了著名的小籠包大型評測;也曾為了尋找鐵鍋的未來與過去,穿梭全國。
在眾多的美食創(chuàng)作者中,他最尊敬的人是袁枚。這個清明節(jié)前,他避開人流,去拜祭自己心中的享樂英雄。這可能不是一次傳統(tǒng)的拜祭之行,但絕對很有趣。
清明快到了,但作為一個住在中國的外國人,我倒是從來沒有什么墓可以掃。
所以今年,我決定去拜祭袁枚。
理由很簡單。袁枚在他的《隨園食單》中寫食物,我也寫食物;袁枚在烹飪上固守己見,我自己也是頑固又事多;袁枚是個享樂主義者;而我也是個享樂主者。
我們唯二的不同,是時空與身份——他是去世距今200多年之久的清朝詩人;而我是個在現(xiàn)代中國的美國前廚師,以及,目前還活著;但是除此之外,我們幾乎是對雙胞胎了。
袁枚是靠詩賦實現(xiàn)了財富自由與社會地位,但是我感興趣的是他的食物寫作。
在袁枚的時代,餐廳雖然存在,但是真正的fine dining,都藏在當(dāng)時官宦精英家里。袁枚作為賓客,見識過許多這樣家庭雇傭的名廚。在遇到鐘意的菜式時,他也會派自家廚師去人家家中潛心學(xué)習(xí)。
也所以,作為當(dāng)時江南一帶名廚技藝高度與食物智慧的記錄,《隨園食單》的偉大是無可比擬的。
他捕捉到了中國飲食歷史中,食物的季節(jié)性和區(qū)域性差異,比現(xiàn)代大部分菜單,更細致地展現(xiàn)了當(dāng)?shù)氐乩硖厣惋嬍沉?xí)慣。
幾百年后的今天,當(dāng)我們的供應(yīng)網(wǎng)絡(luò)足以橫跨全國,乃至全世界;當(dāng)溫室大棚里能種出反季節(jié)的水果蔬菜時,我們的飲食習(xí)慣也許已經(jīng)完全改變,但是能有這樣一份記錄了誰在什么時候耕種了什么的史料,仍然無比珍貴。
他是一位社會地位無可挑剔的高階精英,但卻愿意捍衛(wèi)當(dāng)時社會地位最低的廚師們。《隨園食單》像是對所有廚子的贊賞。
大概這也是為什么,比起讀袁枚的詩詞曲,我更喜歡看他如何描寫竹筍。
為了這次拜祭,我提早做了許多功課。我想要看看他曾經(jīng)生活的園林,他的墓碑,再嘗嘗他的"隨園食單"。
第 1 站
尋隨園
我的第一站,是先去找隨園的故址。
我不認為袁枚會對留存至今的“隨園”感到欣慰——曾經(jīng)坐擁城墻外300畝地的豪華花園,現(xiàn)在是南京市區(qū)廣州路140號。
一對威武的金獅子守在門口,不過大廈里面并沒有值得守衛(wèi)的東西,周遭只有一家餐館、小旅館和酒吧。
不過其實袁枚和我一樣不喝酒,是個頭腦清醒的享樂主義者;)
在大廳里,管理人員在面對我詢問這片土地曾經(jīng)榮光時,很不耐煩地用一句“這兒沒什么歷史”,打發(fā)了過去。
外面是熙攘的車流喇叭聲,街口是正在施工的地鐵口,臨時施工墻與工人宿舍散落在周邊。
這片土地也許曾經(jīng)極其輝煌,未來還可能更加便利,但現(xiàn)在卻與安寧平靜毫不相關(guān)。
一位在隨園大廈邊住了50多年的居民告訴我,如今這片地塊價格約為¥40000/㎡。
雖然能說出自己住在“隨園9號”,聽著確實讓人羨艷,但現(xiàn)實卻很骨感——低矮的公寓樓與眾多的電線桿交織在一起,這座街區(qū)肯定有過更風(fēng)光的時候。
我在這里打開大眾點評時,發(fā)現(xiàn)一家堂而皇之取名為“隨園食府”的餐廳,點進去才知道是一家幽靈檔口,做些廉價外賣。
而街角的肯德基很忙碌——在袁枚的封地上做著炸雞漢堡,這世界還有天理嗎?
第 2 站
尋《隨園食單》
南京很多餐館都借用了隨園的名號,有些甚至復(fù)刻了食單中的菜式。但只有一家隨園五季,得到了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認證。
這也是我們的午餐目的地。
老板倪兆利在袁枚300歲誕辰時開了這家餐廳。房間內(nèi)隨處可見袁枚的詩詞,以巨大的尺寸貼在包間墻上,或裝飾在扇子上,或?qū)懺趶N房門簾上。
午餐時,倪總告訴我們這家餐廳的誕生:附近大學(xué)在研究如何讓中醫(yī)健康飲食倫理進入餐廳時,她被委以這一重任。
作為北京人的她,想起了大學(xué)讀過的《隨園食單》,決定將身為半個南京人的袁枚,以及他的飲食哲學(xué),融入食補體系中。
畢竟袁枚活到了82歲,他一定多少有點經(jīng)驗吧?
不止《隨園食單》,餐廳還汲取了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的“五季”理念(一年有五個季節(jié),夏秋之間還有一個季節(jié)),以季節(jié)和數(shù)字“五”為主題構(gòu)建了菜單:每年有五個菜單,果盤上有五種水果,五種顏色的面條,五個小菜作為開胃菜。
來自北京的倪總和袁枚一樣,自己并非廚師出身,但會參與招牌菜的研發(fā)。比如切成細丁的八寶豆腐,或是用韭菜芽來炒田螺與脆蘆蒿。
但她不是一個完全照搬袁枚菜譜的保守派。在她看來,如果沒有創(chuàng)新,文化遺產(chǎn)就會失去其意義并消亡;傳統(tǒng)需要一點現(xiàn)代元素的融合,才能延續(xù)下來。
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人均500元的套餐中,會出現(xiàn)凍鵝肝吐司,或像牛排一樣擺盤的紅燒牛肉,要配著醬汁和漬番茄一起吃。
這也是為什么有一道菜會是宮保大蝦,白灼鮑魚會用到四川紅油調(diào)味,以及廚房有一位來自廣東江門的燉湯師傅。
吃完午飯后,倪總送我們?nèi)⒂^附近位于廣州路對面的袁枚雕塑。途中,我出于好奇問她:袁枚本人會如何看待隨園五季呈現(xiàn)出的地區(qū)和菜系的融合?
倪總的回答很謹(jǐn)慎,她并沒有聲稱自己做的是隨園菜,她認為隨園菜這個門類太寬泛,沒有什么大意義。
他們是試圖在袁枚的哲學(xué)與食補需求間找到平衡,再在南京食客們愿意接納的食物之間做權(quán)衡。
如此看來,在21世紀(jì)的今天,一邊想更新袁枚的飲食理念,一邊還要保持對他的致敬,也挺不容易。
第 3 站
為袁枚燒一炷香
1798年,在袁枚去世前,他要求家人(包括他62歲時出生的長子,名叫阿遲)用他身后的巨額遺產(chǎn),保證隨園在30年內(nèi)完好無損。
令人欣慰的是,他們成功了,隨園留存的時間遠遠超過了30年。
但在1850年時,太平天國來到了南京。據(jù)《方志南京》的描述,太平天國運動將袁枚的遺產(chǎn)摧毀殆盡。不僅拆掉了園內(nèi)的樓宇亭臺,甚至將旁邊的“太平”小山,都夷為平地。
不過,他們并沒毀掉袁枚的墓。
往后的100年內(nèi),袁枚的墓碑依舊屹立著,直到上世紀(jì)60年代。很顯然,當(dāng)時大家對袁枚這樣封建享樂地主并沒有什么好感。袁枚的墳?zāi)咕痛吮粴В罄m(xù)又重建。
袁枚墳?zāi)沟奈恢茫窃诶_路9號,也是五臺山保齡球館兼江蘇省保齡球運動協(xié)會,這是我拜祭袁枚之行的最后一站。
那天是周六下午,球館里幾乎都是人。
我努力擠進球鞋,挑了一個10磅重的球,還做了些拉伸。默念:這一球,是為袁枚而投。
剛開始投球時,我肌肉很緊張,球往左偏了一些,不幸滑進了滾球道。
這不是我想要的,我想讓袁枚感到驕傲。
我深呼吸幾次,重整節(jié)奏,投球時更努力向下沉身,球沿著球道中央前進,擊中了!我繼續(xù)重復(fù)了一次,兩次,三次,分?jǐn)?shù)越打越高,但時間不夠了,最終拿到了87分。
想必袁枚會諒解這不高的分?jǐn)?shù)——我太緊張,行程也太匆忙,也有段時間沒打保齡球了。
我將鞋子還給前臺,往外走到了吸煙區(qū),一個禿頂老人正往外拿煙。
我從包里掏出了我給袁枚帶的小心意——兩根紅色的小蠟燭。我把它們放在煙灰缸上點燃,老人掃了我一眼。我接著拿了一捆香出來,試著用蠟燭點著香火。
老人決定看向別處。
我搭話道:“袁枚,你認識他嗎?”
老人又瞥了我眼,但沒有說話。
我接著說:“這里曾經(jīng)是他的墳?zāi)梗驮谶@個保齡球館。”
就在這段短暫的對話中,香點著了,開始冒煙。
緊接著租給我保齡球鞋的女士走了出來,質(zhì)問我在做什么。
我努力辯解:“這里曾經(jīng)是袁枚的墓!隨園,袁枚,《隨園食單》!”
她回道:“好吧……那是誰?”
我開始擔(dān)心我們會被視為可疑人士然后被趕出去。然而沒等我回話,她便邊丟下一句:"照片里只要不露出保齡球協(xié)會的牌子就行了。"
接著轉(zhuǎn)身回到了屋里。
一分鐘后她又拿著手機出來了,原來她上網(wǎng)搜到了袁枚的資料。
她很友好,看起來更像是好奇而不是惱火:“這個人,你在紀(jì)念他?”
“是的,”我說,“我們快結(jié)束了,這就走。”
她得到了滿意的回復(fù)后,把我們留在了臺階上
原本我前來想要為袁枚掃墓,但如果找不到一個可以掃的墓,或一座能坐下來的花園,那也只能這樣了——在墳?zāi)股闲藿ǖ谋}g球館外,在這方形煙灰缸里,為他燒一炷香。
香的味道漸漸加重,煙也越來越濃,在人群聚集之前,我熄滅了香火。畢竟我不希望此行會引發(fā)國際事故。
但我希望這些升騰的煙能觸達袁枚,無論他在哪里,這是來自一個享樂主義者對另一個享樂主義者的小小致敬。
也許隨園已經(jīng)名存實亡,但至少對我來說,在那個香火煙氣繚繞的時刻,袁枚并沒有離開。
文 - Chris / 編輯 - 夏桁 mmr
圖 - Graeme Kennedy
實習(xí)生kiki對本文也有貢獻
冷鏈服務(wù)業(yè)務(wù)聯(lián)系電話:1361384128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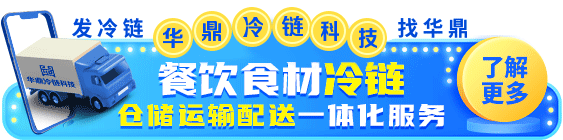
標(biāo)簽:

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 企業(yè)新聞
企業(yè)新聞 展會新聞
展會新聞 物流新聞
物流新聞 冷鏈加盟
冷鏈加盟 冷鏈技術(shù)
冷鏈技術(shù) 冷鏈服務(wù)
冷鏈服務(wù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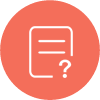 冷鏈問答
冷鏈問答 網(wǎng)站首頁
網(wǎng)站首頁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