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是美食荒漠?片兒川請求出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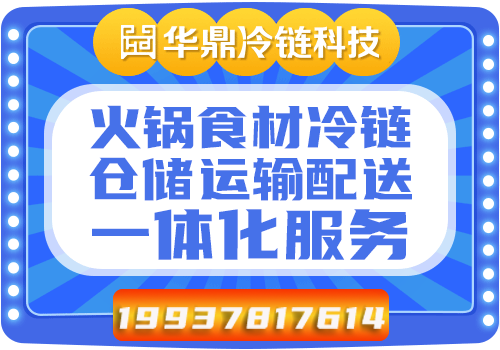
轉自:吳卓平
最近聽到一個真實的笑話:一位北方朋友準備陪家人來杭州踏春,有本地好友介紹他來杭州必須吃一碗片兒川,他一聽就樂了,“啥?屁兒穿!”“那必須得點一份,嘗嘗到底有多辣。”
幽默得太像是一個段子了。
的確,杭州人的這碗面,名字著實可愛,片兒川,既保留著宋人從開封帶來的兒化音,又夾雜著江南人c與ch分不清的特有口音,把汆(cuan)念成了川。
當然,這碗面在杭州人心底的崇高地位,堪比古時進京趕考書生留在家中的那位結發妻——縱使高中狀元、飛黃騰達,身邊鶯鶯燕燕、余音繞梁,可一旦午夜夢回,依然會想起她的素衣盤發,她的一顰一笑,還有她的灶邊爐臺……
恰似在網絡上頂著“美食荒漠”名頭的杭州,近日甚至還因“百萬懸賞令”一度沖上新聞熱搜,但哪怕是抱著“荒漠中尋找綠洲”的心態,每每旅行或出差回來,我依然會去吃一碗面,不然就會有種百爪撓心的感覺。
盡管常去的那家路邊店,如今已成為一片工地,一棟商業綜合體即將拔地而起,雖然心中悵惘,不過好在片兒川此味,一直能吃到,就好像杭州這座城市,不管舊貌如何換新顏,內在氣質倒是沒未變過。
紀錄片《中國故事》的第三集中如此說道:在杭州,宋朝文明恢復了。而一碗尋常的面,用最家常、市井、平靜的方式,為食客們濃縮了一副南北融合的宏偉畫卷。
你看,無論多么驚心動魄的歷史進程,落在吃物上,都是不動聲色的簡單。
還記得2019年的那個深秋,我從中亞旅行歸來,到家已是凌晨2點,疲憊不堪,但一番洗漱之后,竟然硬生生坐等到天亮,再跑去吃了一碗片兒川。倒不是時差在作怪,實在是因為被各種抓飯、烤串“夯實”了近一個月的胃,除卻這一碗面,此時,已容不得他物。
沒錯,雪菜點綴著里脊肉片,與筍片交相輝映,重嶂疊巒在舒展暢游的面條之上,在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早上,這碗面輕輕巧巧地打通了我睡眼惺忪的車馬勞頓和時差困頓。而這種舒適感與通透感,須一種本地化的表達才最為相稱——杭州話稱之為“落胃”(意為:好吃)。
當然,我去的也不是上了什么報紙和電視的網紅店,不過我家附近一家普普通通的路邊店。在杭州,幾乎每一家杭邦面館都會做片兒川,著名的如狀元樓、奎元館,但我覺得,那是“有朋自遠方來”,請客吃蝦爆鱔的地方。而那些網紅店,如菊英面館、方傳面館、慧娟面館,滋味也都不錯,但這些年,隨著杭州這座城市的聲譽日隆,游客量暴增,從前隱于角落頭的平民小館,如今紛紛成為小紅書、大眾點評上熱門的打卡地兒,而出貨量一大,像片兒川這種以小鍋單獨操作為宜的小吃,難免會差點意思。
或小火慢燉、或鍋氣十足的傳統味道,如今漸漸跟不上快速網紅化的餐飲潮流了,這恐怕也是杭州美食頻頻遭人詬病,被迫頂上“荒漠”之名的原因之一,我猜。
事實上,片兒川這種充滿了濃濃市井氣息的吃食,也的確不適合在那種富麗堂皇的廳堂里狼吞虎咽,倒是那些籍籍無名的小面館里,才能體驗最本真的滋味——
菜,必須是干爽微黑、沒有鹵汁的“倒篤菜”,不是這個,就不夠味兒,尤其不能用濕答答的“抱腌菜”,酸味會嚴重破壞整碗面的口感。筍片,同樣是必須的,一年四季,冬筍、春筍、鞭筍、毛筍,總是不會少的,只有秋冬之交,那一個多月的斷檔期,只能用筍干彌補。
這些年,杭州人還把鹵大腸引入了面碗,與片兒川組成了一對CP搭檔。杭邦面的澆頭不同于蘇式面的精致,往往把下水一通熱鍋爆炒了事,市井氣息濃烈。腰花、豬肝、大腸三樣,是最常見的下水配菜。而大腸滑嫩且富有彈性,既可以做澆頭,也可以做底料。
點上一碗片兒川,搭配上大腸澆頭,吃得帶勁;而大腸做底料,就是大腸面,則是另一番享受,鹵大腸和面一起燒,加青菜點綴,大腸給面帶來了鹵汁和油氣,充滿油津津的誘惑。
其實,不僅僅是面碗之中,從街頭餐館,到坊巷菜場,再到媽媽的灶頭,杭州城里到處都藏著口碑滿滿的大腸。就連本地最有影響力的報紙,也甘愿為“全杭州最好吃的大腸在哪里”這樣的選題開辟幾個整版的報道。
我的好友小魚,身為本塘土著、美少女、報社美食記者,曾以一天怒吃四頓大腸的節奏,連刷近二十家本邦面館、菜館,用五個整版報道的恢宏氣勢,繪就一份全杭州不容錯過的“大腸經”攻略。
“工傷”之后,每日僅以白粥、榨菜度日,仍不忘朋友圈作詩一首,聊表心志:“撫額大腸香,不慚世上英。誰能書閣下,白首大腸經?十步啖一腸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扶墻去,深藏功與名。”此等職業精神,可親可敬!
見微知著,或許,從中也可窺見這座城市的性格吧。
作為江南城市里的“另類”,清麗外表之下的杭州,無論是方言還是飲食習慣,都帶著南方土壤里生長出的北方印記,面條的風靡,大腸的興盛,恰是這方水土內在的另一種表達。
所以,如果你正在跟一個杭州人談戀愛,若只去高檔日料或者西餐廳、咖啡館約會,肯定是遠遠不夠的,一定得一起再吃幾碗大腸片兒川。
既見過彼此不矜持的樣子,又更懂這座城市的風物人情,能一起吃大腸的人,一定能幸福攜手到老,嘿嘿嘿。
也強烈建議那位將片兒川念成“屁兒穿”的朋友,最好能跟著本地人一起去吃這碗面。吃得老杭州片兒川,再用杭州“黑話”點單,那種“落胃”的感覺,就來了。
比如,“片兒川,寬湯,重青,油渣要過橋”,只寥寥數語,卻蘊含了好幾個類似英文單詞縮寫的專業術語:“寬湯”是指多加面湯,與之相對的是“緊汁”;“重青”是指多放蔥,與之相對的是“免青”;“過橋”的意思則是配菜另擺一盤,與之相對的是“底澆”。各種名色雖然沒有蘇式面館那么繁復,但這些黑話中自帶市井氣息的情趣,倒是頗為近似。
在我看來,如何更好地融入一座城市?
一是從吃入手,并通過這些鮮味,去觀察一方水土、風貌、民俗、人情,使之成為旅行的線索,二是跟本地朋友多交流,這絕對是可以列入旅行指南的兩大鐵律。
因為,任何一樣吃食,從來不只關乎于吃。情感、記憶、情緒,乃至生活態度,皆牢固地根植于飲食系統中。即使是2023年的今天,在這座以互聯網產業著稱的城市,也還有人聚集在不起眼的小面館外排排坐,拿板凳當桌板,捧著面碗嗦著面,只為真的好吃。
這純粹的美味,好似是從板凳上生長出來一般,此情此景,哪還有半點荒漠的影子,卻真真地讓我為杭州人這種對生活的真摯與熱愛而感動,含淚變胖。
海量資訊、精準解讀,盡在新浪財經APP冷鏈服務業務聯系電話:1361384128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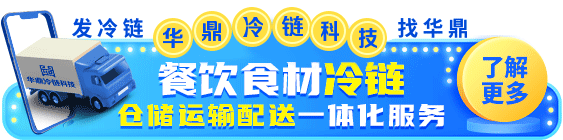
標簽:
食品安全網 :https://www.food12331.com

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 企業新聞
企業新聞 展會新聞
展會新聞 物流新聞
物流新聞 冷鏈加盟
冷鏈加盟 冷鏈技術
冷鏈技術 冷鏈服務
冷鏈服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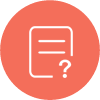 冷鏈問答
冷鏈問答 網站首頁
網站首頁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



